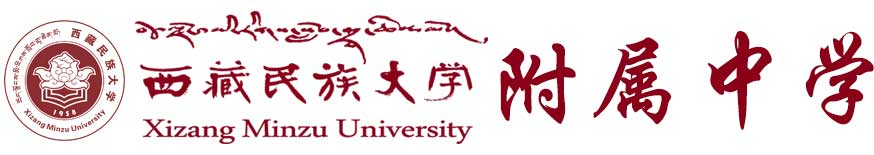您现在的位置:
首页>>党建活动>>学习园地 >>正文内容
学习园地
早期中国神话的破碎本性,盖源于春秋和战国,而非后世儒生所指认的秦朝。这方面的证据来自《孟子》,其中记录了战国时代卫国太宰北宫锜跟孟子的对话。北宫锜求教周朝爵禄如何排列的问题,而孟子则答道:“我也不知详情,因为各国诸侯讨厌这些旧典会妨碍自己的作为,把它们全都毁了。”《孟子·万章下》:“北宫锜问曰:‘周室班爵禄也,如之何?’孟子曰:‘其详不可得闻也,诸侯恶其害己也,而皆去其籍。’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沿用此说称:“及周之衰,诸侯将逾法度,恶其害己,皆灭去其籍,又遭秦火之灾。汉儒附会而成。”(《古今图书集成·二二二卷·礼记部总论》)元朝人吴澄《周礼考注·自序》进一步总结道:“周衰,诸侯恶其害己,灭去其籍。秦孝公用商鞅,政与周官背驰,始皇又恶而焚之。”(《古今图书集成·二三九卷》)自孟子之后,这一说法散见于历代儒家学者的诸多著述之中,但并未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历史发现,恰恰相反,它被淹没于浩瀚的典籍之中,而变得悄无声息。
正是这番出人意料的对白,揭出了翦灭上古文化的罪魁祸首,那就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诸侯们。这个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,为扩张权力、疆土、人口和财帛,努力创立“新制”,推行各种“革命”举措,却苦于孔子之类的守旧派人士的反对,因而焚毁了上古传下来的重要典章,以免被人拿来当作反对改革“新政”的武器。而焚毁的文献,除了孟子提及的周王室的爵禄制度以外,还应包括整个夏(诸夏)、商、周三代的仪典、法规、神话、诗歌和历史。“孟说”虽有为儒家贴金之嫌,但它却足以为第一代神话的亡佚,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。
这种焚毁典籍的恶劣传统,并非只有来自孟子的孤证。《韩非子》宣称,商鞅曾经建议秦孝公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《韩非子·和氏第十三》:“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,设告坐之过,燔诗书而明法令,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,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。”,而韩非子本人对这种焚书之举大加赞叹,声言“明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教”《韩非子·五蠹第四十九》:“故明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教;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;无私剑之捍,以斩首为勇。”意思是明智国王统治的国家,只要以苛法为基准,而须清除掉所有的历史文献。先秦时代的这种焚书原则,显然已被各国统治者所普遍运用,成为消除意识形态异端、架设专制权力的基本策略。韩非子的教诲,更是直接被李斯等人奉为圭臬,为嬴政的“焚书坑儒”提供学理依据。
跟中国历史上众多文化毁灭运动相比,这场运动具有三项重要指征——集体作案、无人领衔、策划者和参与者都难以指认,以致无法就此进行历史审判和文化追究,这种结果为后世的反文化运动,提供了可以热烈仿效的样板。
高度低调和隐秘,几乎不被言说,以致在顾颉刚之前,很少有人发现并谈论它的发生,更由于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成为视觉焦点,这场“犯罪”运动遭到进一步遮蔽。它在历史中隐身,如同它所要消灭的事物。毫无疑问,这是东亚史上发生的首次文化毁灭运动,它企图以“现代性”的名义抹除文化记忆,却导致战国民众跟宗教与历史的断裂,并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,制造了难以逾越的屏障。
“先秦文化革命”具有罕见的彻底性,以致后世无法借助遗址发掘,重新召回那些亡佚的典籍。近百年来的文献考古发现,如少量简牍和帛书之类,多为战国中晚期遗存,而鲜有西周及春秋之物,即便是大规模建设引发的文物出土狂潮,也未能提供任何新的“革命性”发现。最古老的革命,制造了我们最耳熟能详的灾难。
必须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,既然第一代中国神话早已死亡,那么世人现在所面对的,究竟是一种怎样的“货色”?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在战国和秦汉时代重新打造的替代品,混合着早期传说、异域神话和民间想象的碎片。在宗教典籍遭到诸侯湮灭之后,新一代思想者只能面对一个空无的精神废墟,这迫使他们从商人、移民和牧人手里,寻找来自“亚洲精神共同体”的神话资源,以创造性挪用、借鉴、移植、重组与颠覆的方式,勾勒出第二代东亚神学的模糊轮廓,借此完成精神救赎的伟大使命。经过几代文人的拼图游戏,这些可怜的碎片,终于获得了被广泛引用的契机,成为上古意识形态的脆弱徽记。
在上述引入进程中,印度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胡适在其口述自传(唐德刚整理/翻译)中认为,佛教的进入意味着中国的“印度化时代”(Indianization period),胡适为此痛心疾首。但他未能洞察的一个尖锐事实在于,“印度化”其实始于先秦而非南北朝,此外,“印度化”的后果,也不应当仅指佛教,而是包括道家和楚文化等在内的大半个华夏精神体系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联盟,是一个暧昧而坚硬的事实。
但在神话叙事领域,鉴于上古宗教体系的瓦解和缺席,第二代神话只能保持碎屑化的容貌,难以形成神话的内在叙事结构。《山海经》和《楚辞》是其早期代表,前者犹如一幅毫无精神逻辑的地理拼图,浮现出众多“异乡神”(the alien God)的模糊面容,而后者则保留了大量难以索解的问号。至于《古文尚书》,更是汉代或魏晋的“造伪杰作”。这正是所有替代品的弱点——无法真正实现第一代神话的复原,反而制造出更为严重的认知迷津,把人们置于进退失据的困境。
而即便是这种内在混乱的第二代神话,仍然不失为一种文化瑰宝。它的作者大多为各地移民,从美索不达米亚、叙利亚和印伊等地,援引大量“亚洲精神共同体”原型,叙事支离破碎却生机盎然,散发出明快的童年气息。更重要的是,基于非洲原型的基因力量,第二代神话和第一代神话一样,基本沿用了相同的神名音素标记。正是这种识别标记,维系了两代神话的有限连续性。与此同时,在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,新神话所提供的“异乡神”素材,足以支撑中国人的价值信念,以重构民族血缘叙事的基本母题。
这是一场双向的精神运动:一方面是春秋战国诸侯大肆消灭古籍、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和项羽火烧咸阳,这些凶险的事变,导致上古神话的逐级瓦解,形成被洗劫一空的作案现场;而另一方面,战国和两汉文人,孜孜不倦地寻找那些文化废弃物,在捍卫神名音素标记(参见本书第一章)的前提下,以西亚神系和印伊神系为原型,挪用、捡拾、拼贴、填充、重释和新撰,辛勤勾勒第二代神话的模糊轮廓,形成东亚神系的南北两个支系。这种严重分裂的状态,正是人所要面对的文化景观。但鉴于汉儒过于热衷血缘世系叙事,并掀起大规模的“篡经”运动,导致了神话的再度受伤,双向运动虽然有过两个相反的向度,而最终的结局却只有一个,那就是加速中国神话的湮灭进程。最终,人只能无奈地面对掩埋众神尸骸的可笑坟墓。
本文节选自《华夏上古神系》一书
《华夏上古神系》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。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,运用多种学科工具,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,发现并证明,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/神话均起源于非洲,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、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,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,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,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“中国元素”。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,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、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,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,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。
20160308